 今天走到牛棚去看LEGO迷的傑作,
今天走到牛棚去看LEGO迷的傑作,是耐心、是創意,更是熱情,令人讚歎!^o^
(作品是由幾十萬塊積膠砌出來的!)
 |
| 夢幻積膠樂迷城 |
ShumShum Sir's weblog

Why is Raising a White Flag the Symbol for Surrender?
The white flag is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protective sign of truce or ceasefire, and request for negotiation. It is also used to symbolise surrender, since it is often the weaker military party which requests negotiation. A white flag signifies to all that an approaching negotiator is unarmed, with an intent to surrender or a desire to communicate. Persons carrying or waving a white flag are not to be fired upon, nor are they allowed to open fire. The use of the flag to surrender is included in the Geneva Conventions.
The first mention of the usage of white flags to surrender is made during from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D 25-220). In the Roman Empire, the historian Cornelius Tacitus mentions a white flag of surrender in A.D. 109. Before that time, Roman armies would surrender by holding their shields above their heads. The usage of the white flag has since spread worldwide.
Source: 11 Great Color Legends

新式戲院「TheGrandCinema」開幕,戲院從2D走向4D;同期,有「長壽戲院」之稱的皇后戲院宣佈結業。相關新聞: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戲院是男女相約等候的地方。男士們手捧爆穀在戲院門外等候佳人赴約的情況,記者只能在銀幕上看到,但卻是聯邦藝術藏品公司經理鄭寶鴻記憶中深刻的畫面,當年,他與愛人便於戲院內定情。
一張戲票,一張戲橋,不過薄薄一張紙,但對鄭寶鴻來說,卻是滿載回憶的珍貴物品。明天是皇后戲院營業的最後一天,鄭寶鴻不無感嘆唏噓,看著一張張昔日大戲院的舊照,盡訴皇后戲院及已結業大戲院的種種歷史片段與痕跡。
「以前看戲是唯一消遣,更是拍拖好去處。」鄭寶鴻回憶。年輕時的他,曾相約未來太太到皇后戲院︰「女子答允看戲,便是初步接納了你的追求。」他住在中環,到皇后戲院看戲已成習慣,不但常與太太到此,也帶兒女來看如《開心鬼放暑假》、《最佳拍檔》等。
戲院有體重機,小孩子總嚷著要磅重,體重咭上有男女明星相,如夏夢、林黛等,皇后戲院為他一家帶來不少歡樂。鄭寶鴻還笑說,以前皇后戲院地庫有一間夏蕙夜總會,很多人看戲後便到夜總會消遣。
戲橋:不拿吃虧
「我很喜歡看戲,當年港島區約20間、九龍區約60間戲院,我曾到過六成戲院看過戲。」鄭寶鴻說,看戲,少不免有戲票留下:「有些電影會有專製的戲票,如《鬼馬雙星》、《半斤八襾》等,很精緻。以前會把戲票隨手丟掉,回想起來,都是很有意思的藏品,只是需要地方儲藏。」
「以前入場看戲,必會拿一張戲橋。」鄭寶鴻說,一張印著「欲知後事如何,請看電影!」的戲橋,如由樂聲、新聲戲院刊印的《龍虎群英》戲橋,以中英文刊載故事大綱︰「當時拿戲橋的心情很矛盾,不知看好還是不看好。因為看完故事後便沒有興趣看戲,不拿又似乎很吃虧。」最後他還是會拿張戲橋,看完電影後才扔掉。此後十多年,鄭寶鴻收藏了許多與戲院相關的東西,一張張戲院舊照、明信片、戲票、戲橋珍藏起來,昔日看過電影後隨手扔掉的戲票、戲橋,不能重拾,只能一一重新追尋。在那個網絡不發達的年代,印上影片內容,刊登不日放映及下期放映影片資訊的戲橋,成為戲迷們得知最新放映影片資訊的重要來源,但鄭寶鴻最迷戀的,是一幅幅大戲院的舊照及明信片。
舊照:追本溯源
「擁有戲院舊照後便想探本尋源,到圖書館翻看報紙。這張圖片中的民居,前身原是同慶戲園,看19世紀的報紙,會發現這是香港最早的戲院,1867年建成,處於東華醫院對面。1890年改建成重慶戲院,1913年戲院拆卸,變成了民居。這張後期複印的相片,已是70年代的作品。」
舊戲院被拆卸、改建,從本港最早的戲院開始已是不能避免的命運,即將結業的皇后戲院,前身是1911年建成的香港影畫戲院,這間戲院,現在只能從其價值3000元的明信片中緬懷。「10多年前我以695元從一位外國商人買回來,相片中顯示的城市內容,一是香港影畫戲院,二是影畫戲院曾租借附近前身為高等法院的場地作為戲院分院,現為華人行。至1924年,皇后戲院也西化了,掛滿了電影廣告,這張明信片是攝於1950年,以真相作明信片,非常珍貴。現在大家所看到的皇后戲院是1961年建立的,故那時候的皇后戲院只能透過照片一睹。」鄭寶鴻說。
戲票:難忘撲飛潮
戲院在變,戲票也在變。「現在的戲票全是電腦票,昔日則是手寫座位編號的。我花了十多年時間,尋得不同戲院的手劃戲票,各有特色。有的標示了當年戲院的外貌與位置,如凱聲戲院的戲票,一座大廈聳立圖中,兼標示戲院位於旺角彌敦道,查看歷史,原來現址是始創中心的一部分。」鄭寶鴻說。
昔日位於始創中心現址的,還有一間麗聲戲院,是當年全港九最賣座的戲院,曾放映過的電影包括1965年的《叛艦喋血記》。當年附近還有東樂戲院、凱聲戲院,短短的一條街道,已有三間戲院。
鄭寶鴻指,舊戲院分前座、中座、後座、超等、優等等,有的還有特等。戲院可以結業,建築可以被拆,回憶卻依然存在,只是我們需要一些小物件來緬懷。為了尋覓舊戲票,以前較貴的戲票5元一張,鄭寶鴻卻需要花上6倍價錢才能買回自己光顧過的戲院戲票。
鄭寶鴻閒時會拿出這些手劃戲票仔細欣賞,看的是戲票,咀嚼的卻是昔日時光。那些戲院看過甚麼戲,那些電影收費較高,一張張已無法進場欣賞電影的戲票,是記憶的晶片:「《驅魔人》、《教父》、《巴比龍》等,在當年要較其他電影貴。」
「遇到大片上映,戲院一早滿座,便需一早起床『撲飛』,稍遲一點便買不到戲票,看《巴比龍》、《驅魔人》、《半斤八襾》等,便得一早『撲飛』,我便曾試過要看《教父》而買不到戲票。」今日回想,當年為看戲而「撲飛」的回憶,也是一種樂趣。
皇后戲院結業,多年後鄭寶鴻回看相關的戲票、明信片,回憶起的,是一連串的甜蜜故事,那個他曾和太太人約黃昏後的愛情,那個和子女進場的溫馨,不見了建築,卻都封印在那張手劃戲票中。

Shum: 好無奈添,原來傳統節日活動都係在網上搵唔到...連新聞、電台也沒有太多報道呢。似乎「傳統」因為追不了時代而式微了。
所以internet不是萬能...
Tra: 咁d傳統人都仲有好多唔上網...
佢地通知鄉親父老主要唔用呢個途徑,搵唔到都唔奇啦!
自豪是來自他的歷史,他的傳統,「維繫傳統文化」不斷在他的口中重覆。做善事,看到有需要的人拿着平安米、雨傘、水桶、米粉不同的物資的時候,「傳統文化」就是這樣,不是看戲、道士打醮,他最看重的是守望相助,各盡所能,街坊可以捐出自已的物資,雜貨店可捐水桶、做雨傘的可以捐雨傘,沒有物資的可以出一分力陪伴老人家回家。不同的人可以一起參與,形式是次要,當中關係最珍貴。或許保存古蹟文物、傳統節日最重要是詮釋當中的文化意義,探討該事、物的地方意識和如何彰顯其文化身份。如果政府沒有鼓勵民間參與(例如對搞手不太干預,對市民多加宣傳),如果市民沒有認同,只是在粉飾太平而已。

懷念過去常陶醉連下了兩天雨,今天天朗氣清,在粉嶺放學後偷了點時間去看看聯和墟。前天說過名字「富貴」不如「聯和」好,從聯和墟的歷史可知一二。
一半樂事 一半令人流淚
夢如人生 快樂永記取
悲苦深刻藏骨髓......
聯和墟於1949年由粉嶺、沙頭角、打鼓嶺和部分大埔區村民集資成立。1951年正式建墟。建立聯和墟主要是與上水的石湖墟競爭。在此以前,石湖墟是粉嶺及沙頭角、軍地、打鼓嶺一帶鄉民進行交易的市集,但因被墟主上水廖氏多收秤佣或公秤不準確等問題,驅使粉嶺區鄉民建立新墟以保障利益。這個情況就像大埔舊墟被鄧氏壟斷,所以文氏等人在太和開新墟,又像元朗舊墟被錦田鄧族支配,於是十八鄉村民都到隔鄰去開五合街新墟。
罷工第十日(來源)延伸閱讀(聯和墟、《每當變幻時》):
香港是個小天堂 美景熣燦耀香江
四通八達千里路 萬丈高樓映彩雲
棟棟新樓如天柱 通天達地顯辛勞
工人為港流血汗 辛勞血汗流成河
雖受沙士來挫折 工人共渡患難關
十年霜雪身感受 奸商欺榨太無良
今日香港有成就 工人加薪理應當
奸商無恥出下策 不加人工加時間
迫我工人來反抗 出來一齊反奸商
欺榨工人真可恥 還我工資及工時

說寧靜 唐君毅仙館平日遊人不多,三聖殿內太上老君仍在煉丹,邱處機仍在教楊過做人的道理,而呂洞賓呢,仍在被狗咬。(以上全是說笑 ^^')今天他們仨桃李不言,安靜了我俗人一個。XDDDD
人類最高的幸福,是他的寧靜。
在寧靜中,你的思想情緒,在它的自身安住。
在寧靜中,你的性靈生活,在默默的生息。
在寧靜中,你的精神,在潛移默運,繼續的充實它自己。
在寧靜中,你的人格之各部交互滲融,凝而為一,
以表現於你自己心靈之鏡中,而你的心靈之鏡光,能自相映射。
說悲哀 唐君毅沿途感受雨後格外新妍的村落景致,漸漸重回煩囂的都市--石湖墟。
你能避免煩惱,然而世間有不能避免的真實的悲哀,如:離別與死亡,那怎麼辦?
真實的悲哀嗎?他來了,你當放開胸懷迎接他。
煩惱只是擾亂了你的心靈,真實的悲哀,洗去你其他的縈思,淨化了你的心靈。
雨後的湖山,格外的新妍。你的視線,從真實的悲哀所流的眼淚,看出的世界,也格外的晶瑩。
你將更親切的了解世界了。
據說石湖墟的建立可追溯至三百多年以前。早期墟前有一條小河流經,在現時新豐道郵政局附近的位置有幾塊巨石將河水截住,形成一個小湖。石湖墟因以為名。石湖墟初期面積細小,僅有一條稱為「咱婆街」的小街及八間商店。在網上找到一段由學生探究石湖墟的研習。有時這類市集的保育,不只是因為近來被吹捧的概念「集體回憶」,也不是甚麼建築的美。去看看灣仔市集關注組的保育行動,他們告訴了我,舊區重建真的影響到當地小檔販的生計。政府是否有權因為要發展,而去奪取升斗市民的財產?
石湖墟是昔日上水圍廖氏農產品、牲畜及家禽的交易地點,闢有廣大且有上蓋的墟場。每月逢有一、三、五的日子為墟期,鄉民可依時「趁墟」,以作買賣。而每筆交易所得的佣金,則作為墟場的管理費用。1930年代,石湖墟發展為上水的商業及貿易中心。
1955年,墟內一米舖於午夜失火,火勢迅速蔓延,將整個石湖墟的店舖住宅夷為平地。火災以後,鄉民在原地重新搭建房子居住;惜1956年冬,當地再次發生大火,房屋再被燒光。後在紳民的努力下,重新建設石湖墟,於1964年完成。鄉民為了象徵新的開始,於是在重新命名所有街道時,都加上一個「新」字,如新豐路、新健街、新康街、新成街、新功街、新發街、新財街,取健康、成功、發財等好意頭。

 ↑兵頭花園內愛德華像旁
↑兵頭花園內愛德華像旁黃四孃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老鄭回家準備行裝,我則繼續自得其樂。原想找找干諾道填海碑記,卻忘了原來在遮打花園,找了很久也找不到,那麼就隨緣吧。時間尚早,也想想很久也沒有踏足金鐘這邊,於是小弟就在細雨中,漫步了殖民地年代的我城。
流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杜甫《江畔獨步尋花》
 From Jokes on the web
From Jokes on the web梁﹕所以你對皇后的碼頭的感情是很私人的感情?我也相信。
朱﹕是的。但我覺得這份美好又是很多人都能分享,也都應該有權分享的。所以我才會在某天突然想起「為下一代保留此地」這句口號,我真的相信這句話。
公民政治權利是指公民依法享有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權利。它包括以下的內容:延伸閱讀:
.公民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參與國家管理的權利
.政治參與的基本條件是知情權
 ↑簷前獅子「叻到抆」(上水廖萬石堂)
↑簷前獅子「叻到抆」(上水廖萬石堂) 想到粉嶺圍很久,原因是門樓那個令人滿有疑團的三個白點,還有每次也讓我摸門釘的彭氏宗祠。為甚麼「粉嶺」叫「粉嶺」?據說是與大嶺山有關:大嶺山其實是今天華山的別稱,相傳山上有一塊雪白的石壁,於是鄉民稱之為「粉壁嶺」,其後簡稱為「粉嶺」。今天有廖有容所立祈雨碑於華山上,碑上刻寫「大嶺」二字,見證了粉嶺的歷史。(祈雨碑相片請看這個)不過粉嶺的話事人卻是彭族。彭族源自江西廬陵,於宋末逃難至寶安(香港)。族人初於龍山一帶落籍,至明朝萬曆年間定居於粉嶺圍,所以今天正圍的門樓、風水塘和古炮,已大大話話有四百年歷史。正圍門聯「前環鳳水,後擁龍山」依稀述說著粉嶺於梧桐河、龍山的建圍格局。沒有意外的思德書室、彭氏宗祠,依舊重門深鎖。不過天色明媚,能夠照下藍天碧水、灰磚綠瓦的景色,早已是不枉此行。
想到粉嶺圍很久,原因是門樓那個令人滿有疑團的三個白點,還有每次也讓我摸門釘的彭氏宗祠。為甚麼「粉嶺」叫「粉嶺」?據說是與大嶺山有關:大嶺山其實是今天華山的別稱,相傳山上有一塊雪白的石壁,於是鄉民稱之為「粉壁嶺」,其後簡稱為「粉嶺」。今天有廖有容所立祈雨碑於華山上,碑上刻寫「大嶺」二字,見證了粉嶺的歷史。(祈雨碑相片請看這個)不過粉嶺的話事人卻是彭族。彭族源自江西廬陵,於宋末逃難至寶安(香港)。族人初於龍山一帶落籍,至明朝萬曆年間定居於粉嶺圍,所以今天正圍的門樓、風水塘和古炮,已大大話話有四百年歷史。正圍門聯「前環鳳水,後擁龍山」依稀述說著粉嶺於梧桐河、龍山的建圍格局。沒有意外的思德書室、彭氏宗祠,依舊重門深鎖。不過天色明媚,能夠照下藍天碧水、灰磚綠瓦的景色,早已是不枉此行。 上水鄉的話事人姓廖,就是立華山祈雨碑的廖有容族姓。廖有容是上水廖族於清朝道光年間的讀書人,當年他是歲貢身份中朝廷的最高學府。清朝時,每年通過兩次考試成績優異的稱為「廩生」,再獲朝廷遴選入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讀書就是「歲貢」。今天廖有容和他的弟弟神童廖有執,也有數雙功名夾坐落於上水鄉。廖族源自河南,比彭族來粵為晚,於元末散居於今深圳福田﹑新界雙魚﹑橫眉山、上水一帶,並建成村落。萬曆年間傳至七世祖以廖南沙為首,選定龍口地形像鳳之處,鑿池築城,建成「圍內村」,並置三房(二世祖長房如珪、二房如璋及三房如碧)的子孫入圍居住。由於圍內村立於梧桐河之上,廖族便稱其為「上水鄉」,就是「上水」名稱的來歷。上次和家人同來,趁趁六十年一屆的廖族太平清醮熱鬧;今天的大祠堂廖萬石堂則關門休息,水靜鵝飛,寧謐氣氛卻另有風味。
上水鄉的話事人姓廖,就是立華山祈雨碑的廖有容族姓。廖有容是上水廖族於清朝道光年間的讀書人,當年他是歲貢身份中朝廷的最高學府。清朝時,每年通過兩次考試成績優異的稱為「廩生」,再獲朝廷遴選入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讀書就是「歲貢」。今天廖有容和他的弟弟神童廖有執,也有數雙功名夾坐落於上水鄉。廖族源自河南,比彭族來粵為晚,於元末散居於今深圳福田﹑新界雙魚﹑橫眉山、上水一帶,並建成村落。萬曆年間傳至七世祖以廖南沙為首,選定龍口地形像鳳之處,鑿池築城,建成「圍內村」,並置三房(二世祖長房如珪、二房如璋及三房如碧)的子孫入圍居住。由於圍內村立於梧桐河之上,廖族便稱其為「上水鄉」,就是「上水」名稱的來歷。上次和家人同來,趁趁六十年一屆的廖族太平清醮熱鬧;今天的大祠堂廖萬石堂則關門休息,水靜鵝飛,寧謐氣氛卻另有風味。



白田村空前大火毀屋萬間,災民無數。沖天大火傳是由弄炊而起,焚燒歷6小時,火場廣涉3方里,波及石硤尾多個木屋區,在烈燄籠罩下,居民來不及收拾細軟,只能緊抱孩子,往深水埗的方向逃命......戰後由於港人回流和內地人民逃避戰火,導致香港人口急劇增長。人口驟增帶來了屋荒的問題,於是造就了當年漫山遍野寮屋的境況。寮屋的激增又帶來了衛生、醫療、市容,甚至是黑社會問題,令港府的社會政策備受壓力。1953年聖誕節,石峽尾寮屋區發生的大火,令石硤尾村、白田村、窩仔村一帶五萬多人痛失家園。災民為求一宿,於是紛紛在深水埗街道上搭起鐵皮屋。這些「騎樓底」下的寮屋,與樓上的私人唐樓,互相輝映。寮屋問題,反而因大火而擴散起來。
 右圖是石硤尾第一代徙置區於六十年代的地圖,座號以英文字母命名,顯示了該邨樓宇落成的次序。
右圖是石硤尾第一代徙置區於六十年代的地圖,座號以英文字母命名,顯示了該邨樓宇落成的次序。
孫中山紀念館的館址「甘棠第」於1914年建成,原為香港殷商何東胞弟何甘棠的住宅,樓高四層。整座大樓的建築屬英皇愛德華時期的古典風格,弧形陽台有希臘式巨柱承托。內部裝修瑰麗堂皇,色彩斑斕的玻璃窗、陽台牆身的瓷磚,以及柚木樓梯的欄杆至今依然保存良好,是香港現存有數的二十世紀初建築物。甘棠第不單在外觀上美輪美奐,亦是香港其中一座最早以鋼筋構建,並有供電線路舖設的私人住宅,堪稱香港建築史上的里程碑。我從紅磡坐小輪出發,自新的天星碼頭朝著半山邁進。那時,我心裡由衷地多謝了當年被我暗罵浪費電力,建議鋪設登山電梯的人。儘管汗流浹背,踏進甘棠第即有點點elegant的感覺。白廳中美輪美奐的白色金色主調,古雅的科林斯式石柱豎立其中,純樸盎然的柚木大梯與本土氣色的紙皮石地下,全都顯出昔日主人的氣派和對生活質素的追求。腦裡有一刻閃過鄭叔叔家在中山的大宅,回味著那家鄉間退休老者居停的感覺。

4-美國公理會福音堂原址-必列者士街2號我踏著「孫中山先生成長之路」,仍然是那些指示牌,心想為甚麼今次我會耐心地看?回想起早前一眾前輩所導賞的「香港文學散步」,所到之處多是今非昔比,但是他們仍然發思古之幽情,侃侃而談,傾囊以授。我望望面前的指示牌,望望柏油鋪成的地下,心想我是否踏在孫中山或是他們的足蹟呢?這瞬間,眼前的一步一景,盡是value。
1883年孫中山先生在此堂接受洗禮。
5-中央書院原址-歌賦街44號
孫中山先生於1884至1886年間,曾在此校高年級肄業。
6-「四大寇」聚所楊耀記-歌賦街8號
「四大寇」是指孫中山先生及三位志同道合者,四人常聚於楊耀記店內暢談反清革命。
7-楊衢雲被暗殺地點-結志街52號
楊衢雲為香港興中會會長,1901年1月10日在其創辦的英文學館內被廣州清吏買兇暗殺。
8-輔仁文社原址-百子里
輔仁文社由楊衢雲與謝纘泰於1892年所創立。孫中山先生與個別社員接觸頻密,楊衢雲與謝纘泰後來都成為香港興中會的核心成員。
9-皇仁書院原址-鴨巴甸街與荷李活道交界
1884年興建校舍的奠基禮上,孫中山先生亦曾在場。
10-雅麗氏利濟醫院及附設香港西醫書院原址-荷李活道77至81號
孫中山先生於1887至1892年在此校習醫五年。
11-道濟會堂原址-荷李活道75號
孫中山先生在港習醫期間,經常到此參加聚會。
12-香港興中會總會-士丹頓街13號
孫中山先生在此籌組第一次革命起義-乙未廣州之役。


略知中國歷史的人都討厭宋徽宗,《水滸傳》裡水泊梁山上的一百零八條好漢的對頭就是他,後來把北宋斷送在金人手裡的罪魁禍首也是他。宋徽宗算不上是個好皇帝,卻是中國兩千多年封建歷史上346位皇帝中最賦藝術氣質、最才華橫溢者。他的畫流傳到今天的都是國寶。和堅仔去博物館的好處是:他會每事問,反而令我眼中平凡的展品都變得不平凡呢。^^
宋徽宗的藝術才華有哪些證明呢?他自創一種書法字體,被後人稱之為「瘦金書」,另外,他在書畫上署名簽字是一個類似拉長了的「天」字,據說象徵「天下一人」,真是風流得很。不僅如此,他在位時將畫家的地位提到在中國歷史上最高的位置,以畫作為科舉升官的一種考試方法,每年以詩詞做繪畫的題目,曾刺激出許多新的創意佳話。如題目為「山中藏古寺」,許多人畫深山寺院飛檐,但得第一名的沒有畫任何房屋,只畫了一個和尚在山溪挑水;另題為「踏花歸去馬蹄香」,得第一名的沒有畫任何花卉,只畫了一人騎馬,有蝴蝶飛繞馬蹄間。
這些都刺激了中國畫意境的發展。宋徽宗本人也是一位技藝高超的畫家,而且還有自己一套繪畫理論,寫到:「孔雀登高,必先舉左腿。」有趣極了。他廣泛搜集了歷代文物,令下屬編輯《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宣和博古錄》等著名美術史書籍。對今天的人了解中國美術史有相當大的幫助。
宋徽宗最有名的畫作是那幅《瑞鶴圖》,仙鶴在北宋的皇宮上飛翔和駐留,一片祥和氣氛。但這次來香港展出的是他的《祥龍石圖卷》,畫裡的假山石頭形狀如同蟠龍。觀眾在看這幅畫的時候不妨想一想,宋徽宗這樣欣賞假山,背後有沒有什麼故事?有的,《水滸傳》裡不是有個著名的段落就是梁山好漢打劫花石綱嗎?花石綱是什麼?就是古典庭園裡用作裝飾的奇花異石。宋徽宗好懂得享受,他設了一個蘇杭應奉局,專門搜羅民間的奇花異石,用大量船隻一批批運至開封,就稱為花石綱。說不定,那幅《祥龍石圖卷》裡的石頭,就是當年的花石綱之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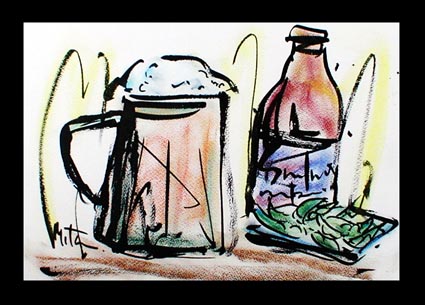 Picture from Mitsuo Yamamoto
Picture from Mitsuo Yamamoto《自由的夢》(MP3)
看那幼小的孩童,沒有天真的記號,
路過說你已長大很高;
何時再接觸到,是你簡單的笑容,
為你我作個自由夢。
那一些是風聲的呼喊?那一天在草地裏奔跑?
風吹遏 搖動夢中的歌,
百萬人期待,讓勇敢遙望著遠山。
你在揮手,握緊每對手,
夢想尋獲自由!
我相信,如果有一天同學願意反省,又或者歉疚的話,原因一定不是因為校方處分了他們,而是我們這些作為老師的,曾經以極大的耐心和誠意,來看待他們所做過的事;如果好多年後,學生仍會惦記著我們的,多半不會是因為我們教授過他們什麼具體知識,而是我們曾經以身作則,教導他們如何處世做人。他看到的是我看不到的。還記得,當天我也曾被老師罵「stubborn」過。
我們都愛自己的學生,但當學生飛黃騰達,名成利就時,我們的愛充其量只是錦上添花;相反,正正是當漫天風雨,壓力鋪天蓋地,學生茫然無助時,我們的愛,我們所表現出的承擔,才是學生最需要的。

My life is nearing its last years, and before leaving this world I just want to try to point out to young people the danger of becoming totally attached to any fundamental group, whether religious or political. There is nothing good in fundamentalism, only personal hurt and harm to others. With open minds, with determination to retain our freedom of thought and action, provided it does no harm to others, we can face all the problems of this life in our own strength and by our own efforts. We do not need to trust man-made remedies, so-called miracles, intimidating teaching. If God exists, no one can honestly know, but we can keep our minds open and fear nothing provided we do good in this world, and in making others happy, we make ourselves happy and able to live fulfilling lives.
Quote from Elsie Tu. (2000) Away with all superstitions: A plea for man to broaden his narrow traditional horizons. Hong Kong: Science & Education Publication Ltd. Ch 16.
 我的小學是天主教學校,中學是天主教學校,大學宿舍是耶穌會辦的;我愛文物,神往於教堂祭典、宗廟建築,向來入廟拜神,入堂喊主,百無禁忌。我們如果明白宗教信仰,本是因為人的宗教精神而衍生,如此我們尊重人的精神,就應尊重各家各派的宗教信仰。
我的小學是天主教學校,中學是天主教學校,大學宿舍是耶穌會辦的;我愛文物,神往於教堂祭典、宗廟建築,向來入廟拜神,入堂喊主,百無禁忌。我們如果明白宗教信仰,本是因為人的宗教精神而衍生,如此我們尊重人的精神,就應尊重各家各派的宗教信仰。
那麼味道也是甘苦交錯的咖啡呢?愛吃朱古力的朋友,對GODIVA這個名字一定不會感到陌生,這品牌三月時在日本推出了四款不同口味的朱古力雪糕,網友讚不絕口。終於等到它們登陸香港,上周我專程往專門店希望一試,誰知卻是一場歡喜一場空,皆因四款新口味中,只有其中三款含牛奶成份的在港發售,獨欠了我最期待的Belgium Dark Chocolate,朋友打趣說:「相信是香港人吃不慣苦,所以黑朱古力沒銷量保證吧!」
也許我是個怪人,吃朱古力獨愛苦苦的,GODIVA價錢太昂貴,只能偶爾用來獎賞自己,平日到超市入貨,我會選日本明治的排裝黑巧克力,它們新近推出了86%濃度的,若不是要顧及家人口味,我還會買99%的,苦到面容扭曲就更高興。
最近電視劇《溏心風暴》裏細鮑有句口頭襌:「甜的也吃,苦的也吃。」(web | video)這句對白真的很有意思。我曾看過一篇文章,說到英文字stressed(感到有壓力)和desserts (甜品)的關係,只要把stressed倒轉來寫就是desserts,生活中的壓力和挫折,表面上是苦的,但換個角度看,它們也是人生中的甜點,讓你的一生更豐富和圓滿。
其實,談戀愛也一樣,你偷偷愛著他,只要他對你笑一笑,給你一句問候,你已經樂上半天;當他跟其他異性玩得忘形時,你站在一旁看得酸溜溜;到他連你的電郵和sms也不回覆時,你簡直痛苦得想哭。要品嚐戀愛的甜味,就要連苦味都一併接收,愛情本來就像享受黑朱古力、黑咖啡和不加糖的橙皮果醬,自討苦吃卻又不知不覺上了癮。
引自張美賢〈甜的吃,苦的也吃〉(頭條日報,2007.05.17)

 林風眠 《火燒赤壁》 1985
林風眠 《火燒赤壁》 1985《觀林風眠速記兩則》 梁寶林風眠 《打麻雀》 1989
經歷抗日與文革洗劫,林風眠的早期作品向剩無幾,早期風格向來只得從黑白照片中管窺一二。這次藝術館「世紀先驅─林風眠藝術展」致力拼湊林氏各個時期面貌,最早一件繪於1938年《販子》,線條粗放直接,有別於後期略帶國畫味的筆法。林氏學藝時期與早期作品應以油畫為主,親眼看過的一件只有 2003年由張永霖藏「林風眠繪畫展」中看過,是50年代末的《養豬姑娘》,只能算是中期作品。這次展覽以主題劃分,展覽大部份以其花鳥及仕女人物作品為主,讓不同時期的作品互相對照,例如把分別繪於1977-78及1989的《打麻雀》放在一起。但我看還是以展場一隅,以特調燈光幽幽地訴說着上世紀的民族苦難為題的五、六件作品最為動人。沿着《打麻雀》之後,掛着的均是繪於1989年的《基督》和《惡夢》系列。尤其《惡夢二》,那血跡斑斑和熊熊火光,粗獷並不來自風格(雖然非常類近德國表現主義),而是源自人性的關懷,看見苦難的切膚之痛。
同日有萬青力先生「寂寞之道:解讀林風眠的藝術人生」的講座,地庫的演講廳座無虛席,有十來個遲來的朋友要靠在牆邊站。投映片開端是林風眠的肖像,寫着「可能是廿十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萬先生卻用當今地球的生態危機作開場白,空氣污染、食水短缺,衛星圖片顯示出北京外圍、珠三角的污染程度為全球之最─才急轉直下,藝術─到底還有什麼意義?於是萬先生講的林風眠,便從他的對人類命運的關懷講起。
平時讀書不求甚解,又或者是讀的著作為賢者忌諱,都說林風眠自幼失怙,一頁便翻過去了。原來林氏失怙,是因母親闕亞帶被族人處以「溺塘」私刑,當時只有七歲的林風眠持刀衝入祠堂救母,父老憐惜其情,改為將其母賣往他鄉,後終生未見。人間慘劇,在林風眠整個人生中留下不能磨滅的暗影,於是重看林氏的「寶蓮燈」與「南天門」,便不再只是戲曲人物那麼簡單。尤其展出作品「南天門」,那種冰冷的藍色主調,鬼影幢幢,寄喻天堂與地獄的生離死別,是對母親的無限追思,卻又超越事件的個別性而直指人類的苦難。林風眠當然亦有少年得志的時侯,以26歲之齡當上美院院長之職,誠為民國初年的特殊處境。(萬先生也幽自己一默,說自己六十歲才當院長,為晚上十一時還不回家的同學而疲於奔命)。然得意的時侯也不過十年,繼後是抗戰、解放、文革,不斷的流徙,與妻女別離,坎坷而耳熟能詳。這些經歷給濃縮成展廳裡獨據一隅的六幅大型作品,萬先生獨對《噩夢─打麻雀》(1977-78/ 1989)作出較為詳盡的說明─這是人類的愚眛,破壞生態、亂殺無辜。萬先生亦認為,這些疲於奔命,最後仍是一一倒下的麻雀,是林風眠一代人的體照,不獨是林風眠個人的故事,而是整個民族的故事。然而,卻只有林風眠一個敢於誠實面對,以藝術來昭示人類的無知,所以林氏是偉大的藝術家。
萬先生主講的部份約只為一小時,卻從林氏的歷史處境和個人命運印證其藝術生命的偉大,不穿鑿附會,不迴避立場。例如有聽眾問林氏1989年作品與民運的關係,萬先生直言「我不知道」,因為無確鑿的資料可證(更順帶指名遠在席間的館長更不能答!)然有關林氏失怙的經歷,卻有真憑實據可證。加上那一代人視藝術如生命,是不會直接繪畫政治題材的。有聽眾更問林氏與徐悲鴻的歷史評價,萬先生認為徐、林二人留法期間同受浪漫主義薰陶,只是在當時以藝術救國的時代需要下,寫實主義無寧是最能為群眾所接受。至於以林風眠比張大千,萬先生則說:「林風眠是知識份子,怎樣跟他比?」演講與對話間更不乏對我們處身的社會和時代的尖銳針砭,萬先生是親身示範何謂藝術對人類、對當代文化的責任。對於中國當代藝術的亂象,萬先生認為我們還是還媒介與西牽着鼻子走─當代藝術就是關心當代文化的藝術,搞藝術不是要引人注意,這想法很幻稚!
我不是主張以人格來判別藝術成就,也不是要放大社會、人類的陰暗面。只是我們今日實在有太多無關痛癢、可有可無的藝術作品。我不是要為林風眠以至萬先生歌功頌德(萬先生回應主持「萬先生是中國現代藝術的權威」,開咪劈頭便說:「我不是什麼權威,只有權威的社會才需要權威」),只是我太久沒有聽過像這樣情理兼備,把人格當成一回事的藝術講座!當大家都把藝術視為發財產業,我倒懷念起老套而純情的人文關懷。
 ↑麟峰文公祠一隅
↑麟峰文公祠一隅 |
| 溫故知新之旅:新田考 |

有錢不就代表富有。很多富人天天愁眉苦臉,惶惶不可终日。反而窮人可以笑口常開,活得快樂充實。要自己快樂,先要別人生活因你變得快樂;要自己生活充實,先要別人生活因你變得充實。明天開始給身邊的人多一聲招呼,多一個笑容,多一次讓座…,並留意他們對你的回應,也許你已能感受我在講甚麼。要活得精采,必多無私地服務他人。這可能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不過,是否通常人在物質豐富後,才去追求精神富有?又或者追求精神富有的人,通常都已經不愁物質?那我可想不通了......




鄧自明與皇族的淵源
南宋建炎三年(1129),金兵再犯江南,宋朝皇室中人流散至贛州。太后帶著高宗兒女路經江西虔州時,不幸走散。當時,任贛縣令的塘尾鄧氏七世祖鄧元亮在江西奮起勤王,平定戰亂。他收留了一批失散的南逃官員子女,高宗之妹——年僅八歲的趙氏就在其中。但幼女不肯將身世相告,只說自己是中州趙姓官員之女。
鄧元亮歸隱嶺南家園後,將趙女撫養成人。親戚朋友見過趙女的,都驚奇她的舉止出眾,就撮合趙女嫁給元亮的兒子鄧自明。她嫁給鄧自明後,生下林、杞、槐、梓四個兒子,定居錦田。
宋孝宗已丑年(1169),鄧自明去世,趙氏撫育四子成才。當時宋光宗(1190)即位,而趙氏也步入老年。後來,她寫了封信,叫大兒子找皇上認親。光宗查識認證後,大為感動,立即派人迎接趙氏入宮,並稱其為皇姑,封為郡主,追贈鄧自明為稅院郡馬。
稅院,宋代掌管關稅、貿易的官員,稱為「商稅院」。郡馬,因鄧自明娶宋朝宗室女為妻,俗稱為「郡馬」。宋歐陽修在《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七•歸田錄》記:「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為縣馬,不知何義也。」
長子鄧林授迪功郎,其餘三子封為國舍郎。皇帝還贈了四十頃田地給趙女為終身之養,可趙皇姑只留下少許,其餘都分給了當地百姓……
皇姑辭歸京師,仍居東莞。由於鄧氏得姓南陽,而鄧自明又為稅院郡馬,所以錦田、廈村等祠堂、村屋,都會寫有「南陽世澤,稅院家聲」意思的對聯。
鄧自明死後葬於凹頭「狐狸過水」,皇姑趙氏則葬於東莞「獅子滾毬」,「狐狸過水」側有皇姑的衣冠塚,以示夫婦永在一起。


難題一推動文物保育是一件困難的工作。
師:點解依度有三隻蟹既?
生:唔記得左......
師:一定有得解。咁蟹背脊有咩野呢?- -'
生:殼囉!
師:文雅d呢?
生:甲!
師:咁三隻蟹加埋呢?^^'
生:三甲!^o^
難題二
師:依到有隻雞噃,點解既?
生:!!!......(完全唔知)
師:通常雞會啼既。
生:......(小學生都知)
師:咁即係識鳴叫啦。咁通常公定乸會啼呢?
生:當然係公啦。
師:咁就即係公會鳴囉。^o^
生:「公鳴」?係喎!^o^
 |
| 古宅墓穴覽勝 |
 在屏山文物徑的盡頭,聚星樓不遠處有一幢兩進三間的古建築。它低陷在泥地以下,雜草齊腰,污水長淹,怎麼看都是一所殘舊古宅,等待歷史將它吞噬。
在屏山文物徑的盡頭,聚星樓不遠處有一幢兩進三間的古建築。它低陷在泥地以下,雜草齊腰,污水長淹,怎麼看都是一所殘舊古宅,等待歷史將它吞噬。 |
| 另類的屏山 |
 長假後學生都是睡眼惺忪的,連我也是。
長假後學生都是睡眼惺忪的,連我也是。一起床洗臉的水,關水務署事;
然後去個方便,關渠務署事;
天氣有點清涼,不如聽收音機的天氣預告,關天文台、香港電台事;
落街返校有完善的道路交通系統,關運輸署、路政署事;
返學我們受九年免費教育,關教統局事;
書簿車船津貼,關學生資助辦事處事;
吃飯的飯商需要監管,關食環署事;
放學後想起海外的友人,要寄生日卡給他,關郵政署事;
然後到康文署的公共圖書館找資料;
影印書本時差點影多過十分一,關知識產權署事;
另外記得星期六會約同學行山,要預備政府新聞處的政府書店繪製的郊遊圖;
回到家裡,看看窗外房屋署所管理的公屋林立;
打開電視,看到有些電視劇演出過火,於是致電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投訴......
猛然記得,今天沒有給人打劫,因為有香港警隊。
想著想著,明天不想返學,不如去看街症......